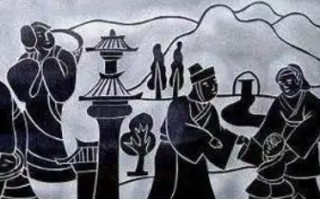在唐朝开元盛世的辉煌图景中,张说以三度拜相的传奇经历和文治武功的卓越成就,成为连接武则天晚年与唐玄宗盛世的枢纽人物。这位出身河东的士族子弟,其人生轨迹与初唐至盛唐的政治变革深度交织,其文学造诣与政治智慧更在史册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一、仕途初启:从制科魁首到政治漩涡
张说生于唐高宗乾封二年(667年),父为八品洪洞县丞。永昌元年(689年),他以弱冠之年参加制科举,策略夺魁,成为武则天时期最年轻的制科状元。初授太子校书郎,迁左补阙,后参与编撰《三教珠英》,与徐坚共同完成这部集儒释道三家经典的巨著。然而,长安三年(703年)的政治风暴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——因拒绝诬陷宰相魏元忠,张说被武则天流放岭南钦州,这场“魏元忠案”成为其仕途的首个重大转折点。
中宗复位后,张说被召回朝,任兵部员外郎,累迁工部、兵部侍郎。景云二年(711年),他升任宰相,加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监修国史。但因拒绝依附太平公主,他很快被贬为尚书左丞,这场与权倾朝野的太平公主的博弈,暴露了初唐政治的复杂性。
二、军事功业:平叛安边与制度革新

张说的军事才能在其政治生涯中多次显现。开元四年(716年),他以荆州长史身份安抚同罗、拔曳固等部,成功化解因朔方大使王晙诛杀突厥降户引发的九姓部族恐慌。开元十年(722年),他任朔方节度使,讨平康愿子叛乱,并建议裁撤镇军二十余万,整顿府兵制,推动募兵制替代府兵制。这一改革不仅缓解了边镇兵力冗余问题,更使“兵农合一”的府兵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
在处置党项问题时,张说展现其政治智慧。开元九年(721年),胡贼康待宾叛乱,他统兵万人出合河关,大破叛军后却拒绝副使史献诛杀党项的建议,转而奏请置麟州安置党项余部。这种“推亡固存”的治理理念,既符合儒家仁政思想,又为边疆稳定奠定基础。
三、文坛领袖:燕许大手笔与开元文风
作为唐代文坛的标志性人物,张说与苏颋并称“燕许大手笔”,执掌文坛三十年。他主持编纂《唐六典》《初学记》《大唐开元礼》等典籍,其中《唐六典》成为中国古代行政法典的典范,《初学记》则为唐代类书之冠。其文学创作涵盖碑志、山水诗、赠答诗等多种体裁,现存诗作140余首,尤以贬谪岳州期间创作的《岳州西城》等山水诗为代表,展现了盛唐气象的雏形。
张说对文学后进的培养亦功不可没。张九龄、贺知章、王湾等盛唐诗人皆受其提携,其倡导的“风骨”“意蕴”诗风,直接影响了开元诗坛的审美取向。玄宗曾亲自为其撰写神道碑文,评价其“发明典章,开元文物彬彬,说居力多”。
四、权力博弈:三起三落与晚年致仕
张说的政治生涯充满戏剧性。他因不肯党附太平公主被贬,又因与姚崇的政治斗争被贬为相州、岳州刺史。在岳州任上,他创作了大量山水诗,这些作品既反映其贬谪心境,也预示着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兴起。开元九年(721年),在苏颋举荐下,他重返中枢,任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,最终拜中书令,封燕国公。
然而,其暴躁脾气与贪财之名终致仕途坎坷。开元十五年(727年),他因遭弹劾被勒令致仕,两年后复任集贤殿学士,主持修撰《谒陵仪注》。开元十八年十二月戊申(731年2月9日),张说病逝,享年六十四岁,获赠太师,谥号文贞。
五、历史回响:功过评说与文化遗存
后世对张说的评价呈现复杂性。一方面,他推动募兵制改革、裁撤冗兵、整顿边防,为开元盛世奠定制度基础;另一方面,其性格缺陷与贪财之名常遭诟病。《旧唐书》称其“刚而犯上”,《新唐书》则肯定其“雅有词藻,尤工碑志”。
在文化遗存方面,洛阳万安山南麓的张说墓志铭由张九龄撰文、梁昇卿书丹,成为研究唐代书法与墓志文化的重要实物。其文学思想与政治实践的双重遗产,至今仍是唐代政治史与文学史研究的焦点。
张说的一生,是唐朝由初唐向盛唐转型的缩影。他从制科状元到三朝宰相,从岭南流放者到文坛宗师,其宦海沉浮折射出唐代政治的残酷与机遇,其文学成就则预示着盛唐文化的繁荣。这位“文能提笔安天下,武能上马定乾坤”的传奇人物,最终以“文贞”谥号载入史册,成为唐朝历史中不可磨灭的文化符号。
标签: 历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