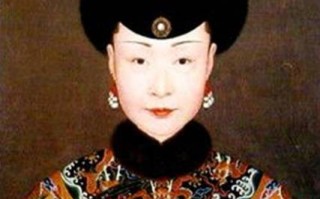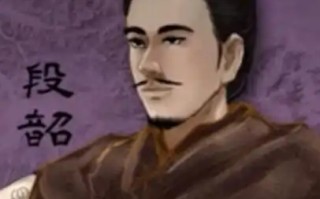在岭南大地的历史迷雾中,南越文王赵眜(又名赵胡)的名字始终笼罩着神秘色彩。这位南越国第二代君主,其名讳在《史记》中记载为“赵胡”,却在1983年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的玉印上赫然刻着“赵眜”。二者究竟是同一人,还是史书记载的误植?这场跨越两千年的身份之辩,实则暗含古代帝王避讳制度、多民族交融与文献传抄失实的复杂逻辑。
一、考古实证:玉印与史书的时空对话
南越王墓的发掘为解开谜团提供了关键线索。
墓主身份的铁证
墓中出土的“文帝行玺”金印、“帝印”玉印与“赵眜”玉印,构成墓主身份的三重认证。其中,“赵眜”玉印为覆斗式印钮,印文清晰,与《史记》所载“赵胡”形成直接冲突;
学者麦英豪、黄展岳等人在《西汉南越王墓》中指出,玉印出土于墓主腹部与腿部之间,属贴身随葬品,其“赵眜”之名应无争议。
名讳差异的三种可能

音义通假说:赵眜的“眜”与“胡”在古音中存在通假关系。例如,《说文解字》释“眜”为“目不明”,而“胡”在古越语中或指“君主”,二者可能因方言差异被混用;
一人两名说:赵眜在南越国内称“赵眜”,对外则使用“赵胡”以避讳。类似案例可见于汉宣帝刘询(原名刘病已)与汉平帝刘衎(原名刘箕子),均因原名不雅或需避讳而改名;
传抄失误说:司马迁《史记》与班固《汉书》在传抄过程中可能因字形相近(如“眜”与“眛”的混淆)导致讹误,后世学者沿袭错误,形成“赵胡”的固定称谓。
二、制度溯源:南越国的汉化与避讳传统
南越国虽为割据政权,却深度模仿中原制度,其帝王名讳问题亦受此影响。
避讳制度的南越实践
南越国官制、礼乐制度均仿效汉朝。例如,墓中出土陶器刻有“长乐宫”“私官”等汉制官署名,证明其行政体系与中原高度一致;
帝王避讳在汉朝极为严格,如汉文帝刘恒在位时,全国需避“恒”字,改“恒山”为“常山”。赵眜若为南越“文帝”,其本名“眜”可能因“目不明”之义而被视为不吉,遂改用“胡”以示尊贵。
双名背后的政治隐喻
“赵眜”为越人本名,反映其族群认同;“赵胡”为汉名,体现对汉朝的臣属姿态。这种“一国两制”的命名策略,既满足南越国内部统治需要,又符合汉朝对藩属国的礼仪要求;
类似案例可见于匈奴单于,其本名与汉廷赐名常并行使用,如呼韩邪单于的本名“稽侯珊”与汉名“知牙师”并存。
三、文献迷局:史书记载的矛盾与重构
《史记》与《汉书》的记载差异,进一步加剧了名讳之谜的复杂性。
司马迁的记载困境
《史记·南越列传》明确称南越文王为“赵胡”,但未提及“赵眜”。司马迁获取信息或源于汉朝官方档案,而南越国对内可能仍使用“赵眜”之名;
学者余天炽等人在《古南越国史》中提出异议,认为《史记》对南越国历代君主事迹记载详实,若“赵胡”为误记,则与全书严谨性矛盾。
后世学者的纠偏与争议
清代学者朱彝尊在《曝书亭集》中首次提出“赵胡即赵眜”的假设,但未提供直接证据;
现代考古学则通过“赵眜”玉印与“文帝行玺”的共存关系,证实二者为同一人。然而,仍有学者坚持“赵眜为赵胡之父”的观点,认为墓中“泰子”印分属父子二人,但此说因缺乏实证而未获主流认可。
四、文化隐喻:名讳背后的文明交融
赵眜与赵胡的双重名讳,实为南越国多民族融合的缩影。
越汉文化的双重烙印
“赵眜”之名可能源于越人语言,如“眜”在古越语中或指“君主”或“光明”,反映其族群身份;“赵胡”则完全汉化,体现南越国对中原文化的深度认同;
墓中出土的丝缕玉衣、编钟编磬等汉式器物,与越式铜鼓、人俑共存,证明南越国在制度与文化上实行“汉越并行”的二元治理。
名讳政治的深层逻辑
赵眜以“赵胡”之名与汉朝交往,既是对“藩臣”身份的强调,亦是对南越国“内帝外王”政治格局的维护。其向汉武帝上书称“不敢擅发兵抵抗”,却暗中遣子入质,实为在汉廷威压下寻求生存空间的策略;
这种“名实分离”的命名策略,在后世藩属国中屡见不鲜,如朝鲜王朝君主对明朝自称“小邦”,对内则称“大君”。
标签: 历史